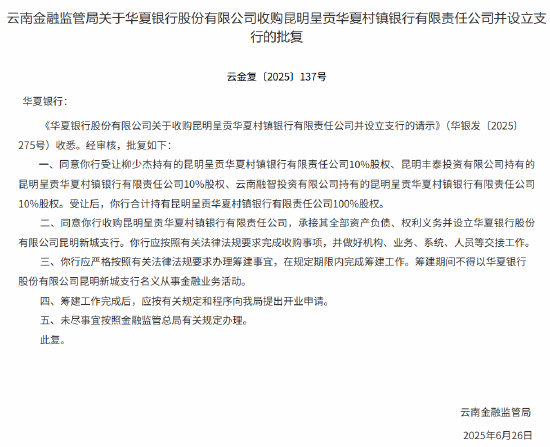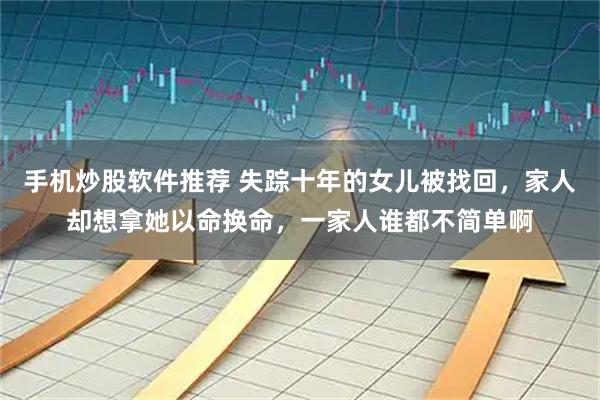
十年手机炒股软件推荐。
整整三千六百多个日夜,足以让一座城市改头换貌,让一个家庭支离破碎,也让一份希望被磨蚀得只剩下一层灰白的底子。
女儿张小雅五岁那年在家门口的巷子口失踪,就像一滴水蒸发在烈日下,再无痕迹。
妻子王桂芳的眼睛,从那以后就再也没真正亮起来过。
而我,张建军,活着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找到她,无论生死。
直到那个平常的午后,一通电话如同惊雷,劈开了我们死水般的生活。
小雅找到了,还活着。
巨大的狂喜如同海啸般淹没了一切。
然而,这喜悦的浪潮退去后,露出的却不是温暖的沙滩,而是冰冷尖锐、令人不寒而栗的礁石。
我至亲的家人,竟然在暗中盘算着,要拿我刚刚失而复得的女儿,去换另一个人的命。
第一章:失而复得
电话是打到我那间狭小的五金店里的。
展开剩余97%老旧座机的铃声嘶哑又急促,像是催命符。
我正给一个锈死的水龙头拧生料带,手上沾满了油污和铁锈。
王桂芳在里间糊着火柴盒,这是她这些年来唯一能做得下去、也勉强能贴补点家用的零活。
“喂,张建军五金店。”
我夹着话筒,肩膀和脑袋歪着,手上没停。
对方的声音很官方,带着一种程序化的冷静,却说着能把我点燃的话。
“是张建军先生吗?这里是市公安局打拐办。关于您女儿张小雅失踪一案,我们近期通过数据库比对,有了重大发现……”
我手里的水龙头“哐当”一声砸在水泥地上。
声音惊动了王桂芳,她探出头,苍白的脸上带着询问。
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只能捕捉到几个关键词:“……找到了……活着……福利院……初步确认……需要你们来辨认……”
电话是怎么挂断的,我完全不记得了。
我僵在原地,像一根被雷劈中的木头,浑身的血液似乎一瞬间冲上头顶,又瞬间冰封。
“谁……谁的电话?”王桂芳擦着手走出来,小心翼翼地问。
十年煎熬,让她对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变得敏感又恐惧。
我缓缓转过身,看着妻子过早爬上皱纹的脸和那双灰蒙蒙的眼睛。
嘴唇哆嗦了半天,才发出一点嘶哑破碎的声音。
“桂芳……小雅……他们说……找到小雅了……还活着……”
王桂芳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
她猛地向前踉跄一步,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建军,你别骗我!你别吓我!”
“没骗你!是真的!公安局来的电话!让我们现在就去!”
我反手抓住她冰凉颤抖的手,语无伦次,“走!快走!去公安局!”
我们甚至忘了锁店门。
像两个疯子一样,跌跌撞撞地冲上街头,拦下一辆出租车。
一路上,我们都紧紧攥着彼此的手,指甲掐得对方生疼,却谁也不敢松开。
仿佛一松开,这个巨大的美梦就会惊醒破碎。
王桂芳的眼泪无声地往下淌,身体一直在发抖。
我盯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心脏狂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十年了。
我们想象过无数种可能,好的,坏的,甚至是最坏的那种。
但“她还活着”这个消息,依旧像一颗核弹,在我们早已荒芜的心原上炸开,带来毁灭,也带来一种近乎绝望的希望。
第二章:裂痕初现
在公安局那间灯光惨白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她。
她坐在椅子上,很瘦小,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旧衣服。
头发枯黄,低着头,双手紧紧绞在一起,指节泛白。
和她一起进来的女警温和地对她说:“小雅,你看,谁来了?这是你的爸爸妈妈。”
她慢慢地、极其缓慢地抬起头。
那张脸,依稀还能看到五岁时眉眼轮廓的影子,但已经完全长开了。
更让人心头一刺的是,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深井,看不到底,也映不出我们的影子。
王桂芳“哇”地一声哭出来,扑上去就想抱她。
“小雅!我的孩子!妈妈想死你了!我的小雅啊……”
女孩像是受惊的兔子,猛地往后一缩,躲开了王桂芳的拥抱,身体瞬间绷紧,眼神里闪过一丝清晰的恐惧和抗拒。
王桂芳的拥抱僵在半空,哭声也卡住了,脸上是巨大的错愕和受伤。
我的心狠狠一揪。
赶紧上前拉住妻子,声音干涩地打圆场:“孩子刚回来,不适应,慢慢来,慢慢来……”
办理手续的过程,我几乎都是懵的。
只知道机械地签字,按手印。
耳朵里听着警官的介绍,说孩子是在一次跨省行动中被解救的,之前一直生活在很偏远闭塞的山村里,吃了不少苦,性格内向,让我们一定要有耐心,好好补偿她。
我的眼睛,却一刻也离不开那个缩在椅子角落、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气息的女孩。
她是我的小雅,可她又完全不是我想象中女儿该有的样子。
我想象过她甜甜地笑,扑进我们怀里撒娇。
想象过她哭着诉说这些年的委屈。
唯独没想过,她会是这样一副被抽空了灵魂的木偶模样。
带她回家的路上,她一直紧贴着车窗坐着,尽可能离我们远远的。
问她什么,她要么点头,要么摇头,最多发出一个简单的音节。
家里的亲戚闻讯都赶来了,小小的屋子里挤满了人,七嘴八舌,洋溢着一种夸张的、喧闹的喜庆。
“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建军桂芳,你们总算熬出头了!”
“小雅都长这么大啦!还记得大伯吗?”
“真是老天开眼啊!这下咱们老张家团圆了!”
小雅被围在中间,像一只被围观受惊的小兽,头埋得更低,身体微微发抖。
我赶紧把大家都劝开了。
热闹一直持续到晚上才散去。
家里终于安静下来。
王桂芳红着眼圈,在厨房里忙活,做了一大桌子菜,全是小雅小时候爱吃的。
她把菜一样样夹到小雅碗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吃,孩子,多吃点,你看你瘦的……”
小雅拿着筷子,拨弄着碗里的菜,吃得很少,很慢。
夜里,王桂芳想陪小雅一起睡,却被她无声地、坚定地拒绝了。
她把自己关在了那间我们为她保留了十年、却无比陌生的房间里。
我搂着默默垂泪的妻子,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最后都汇成一种沉甸甸的、无法言说的涩。
找回女儿的巨大喜悦,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冰冷的隔阂悄然侵蚀。
第三章:隐秘的盘算
找回小雅的第三天,弟弟张建国和母亲从老家赶来了。
张建国的气色很不好,脸色蜡黄,眼袋浮肿,走路似乎都有些喘。
他比我还小五岁,看上去却比我苍老许多。
母亲一进门,目光就越过我们,精准地落在了角落里沉默发呆的小雅身上。
那眼神复杂极了,有关切,有审视,但更多的,是一种让我心头莫名一紧的、灼热的探究。
她上前拉住小雅的手,语气是夸张的心疼。
“哎哟,我苦命的孙女哦!瞧瞧这小手糙的,吃了多少苦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奶奶以后一定好好疼你……”
小雅又一次僵硬地抽回了手。
母亲脸上的笑容顿了顿,但很快又恢复如常。
她转而对我叹了口气。
“建军啊,小雅找回来是天大的喜事。可你看看建国……这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张建国有慢性肾病,好几年了。
我一直知道,也时常寄钱回去给他看病。
但最近店里生意差,找小雅又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已经很久没给他钱了。
“哥,嫂子。”
张建国咳嗽了几声,声音虚弱,“恭喜你们啊,小雅回来了,真是……真是太好了。”
他说着“太好了”,眼神却时不时地飘向小雅,那眼神深处的东西,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王桂芳忙着给他们倒水,脸上带着愁容。
“建国的病……最近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母亲立刻接话,像是早就等着这一句。
“还能怎么说?药就没断过!花钱跟流水似的!上周去省城复查,医生说了,再这么拖下去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换肾。”
最后两个字,她压低了声音,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我心上。
换肾。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巨额的手术费,还有,至关重要的肾源。
“哪那么容易啊……”
我干巴巴地说,“肾源要等,手术费也不是小数目……”
“肾源……”
母亲重复了一遍,目光又一次,极其自然地,落在了小雅身上。
那目光不再是奶奶看孙女的目光,而像是在评估一件物品,一件……有可能匹配的“零件”。
小雅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令人不安的注视,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
我的心猛地一沉。
一个可怕又荒谬的念头,如同毒蛇般钻入我的脑海。
但我立刻强行把它压了下去。
不,不可能。
一定是我想多了。
母亲和弟弟只是来看看小雅,只是顺便提一下病情。
他们怎么会有那种想法?
小雅可是他们的亲孙女,亲侄女啊!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这种令人窒息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母亲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
“听说亲属之间配型成功率最高了……”
“一家人嘛,血脉相连,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小雅这身体看着底子还行,养养就好了……”
张建国看小雅的眼神,也变得越来越焦灼,充满了某种濒死之人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渴望。
王桂芳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夜里偷偷问我。
“建军,妈和建国……他们老是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着心里直发毛?”
我只能安慰她,也安慰自己。
“别瞎想,他们是病人,心里着急,口不择言罢了。”
但我心里的不安,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我试图和他们沟通。
“建国的病,我们一起再想想办法,钱我再去借……”
“小雅刚回来,身体心理都没恢复,经不起折腾……”
母亲却总是打断我。
“建军啊,你弟弟可是你亲弟弟!他现在就等着救命的!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
她说着就开始抹眼泪。
“小雅是我们家的人,她享了十年福吗?现在家里需要她,她出份力怎么了?检查一下身体又不会怎么样!”
“检查一下身体”。
她说得那么轻描淡写。
我却听得浑身发冷。
我知道,那绝不仅仅是“检查一下”那么简单。
第四章:摊牌与挣扎
危机在一个周末的晚饭后彻底爆发。
小雅早早回了房间。
王桂芳在厨房洗碗。
母亲、张建国和我坐在客厅里。
气氛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张建国剧烈地咳嗽了一阵,喘着粗气,脸色灰败。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一种近乎疯狂的哀求。
“哥……我……我快不行了……”
他声音嘶哑,“医生说了,再等不到肾源,我可能……可能就下半年的事了……”
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这是我一起长大的亲弟弟。
母亲在一旁啪嗒啪嗒地掉眼泪。
“建军,你就真这么狠心?你弟弟才三十五岁啊!你真要看着他死?”
我痛苦地抱住头。
“我能有什么办法?肾源是说有就有的吗?钱呢?手术费起码二三十万,我去哪里抢?”
“肾源……现成的就有啊!”
母亲猛地抓住我的胳膊,指甲抠得我生疼。
她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压低了声音,却字字清晰,像淬了毒的针。
“小雅!让小雅去配型!她是亲堂妹,希望很大!”
她终于把那个盘算已久的念头,赤裸裸地说了出来。
虽然早有预感,但亲耳听到,我还是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从头凉到脚。
我猛地甩开她的手,霍地站起来。
“妈!你疯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小雅她才十五岁!她刚回来!她受了多少苦你不知道吗?你怎么能打她的主意!”
我的声音因为震惊和愤怒而颤抖。
“我怎么不能打她的主意?她是我孙女!她的命都是老张家给的!”
母亲也激动起来,声音尖利,“她现在健健康康的,捐一个肾又不会死!她救她叔叔的命,不是天经地义吗?难道她的一条命比你弟弟的命还金贵?”
“这不是谁比谁金贵的问题!”
我气得浑身发抖,“这是犯罪!是缺德!她还是个孩子!我绝不同意!”
“张建军!你个没良心的!”
母亲指着我骂,“我白养你这么大了!你只顾着你女儿,你不管你弟弟的死活!你的心让狗吃了吗?”
张建国在一旁喘着气哭。
“哥……求求你了……我不想死……让小雅试试吧……求你了……”
这时,王桂芳听到动静从厨房冲出来,脸上煞白。
显然,她听到了大部分。
她冲过来,像护崽的母鸡一样,对着母亲和弟弟哭喊。
“不行!绝对不行!谁也别想动我女儿!谁也别想!你们这是要她的命啊!出去!你们都出去!”
场面彻底失控。
哭喊声,咒骂声,哀求声,混作一团。
“都别吵了!”
我猛地大吼一声,胸口剧烈起伏。
我看着眼前涕泪横流、面目扭曲的母亲和弟弟,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和陌生。
他们不是来分享喜悦的。
他们是来索命的。
向我刚刚失而复得的女儿索命。
我指着门口,用尽全身力气,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出去。”
母亲和弟弟惊愕地看着我,仿佛不认识我一样。
“滚!”
我又吼了一声。
母亲脸色铁青,嘴唇哆嗦着。
“好!好!张建军!你真有本事!我们走!你就等着给你弟弟收尸吧!我看你后半辈子能不能安心!”
她搀扶着哭哭啼啼的张建国,摔门而去。
屋里瞬间死寂。
只剩下我和王桂芳粗重的喘息声,以及从里间门缝里透出的、死一般的寂静。
我们猛地意识到,小雅可能听到了这一切。
王桂芳腿一软,瘫倒在地,无声地痛哭起来。
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巨大的痛苦和绝望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一边是濒临死亡的亲弟弟,一边是受尽磨难、刚回家的女儿。
这个选择,太过残忍。
我从没想过,女儿历尽劫难归来,等待她的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另一个需要她献祭血肉的深渊。
第五章:无声的抗争
那场激烈的冲突之后,家里陷入了令人窒息的低气压。
母亲和弟弟没有再上门,但电话却像索命符一样,每天准时响起。
铃声一遍遍嘶吼,诉说着那边的绝望和谴责。
我不敢接,也不敢完全拔掉电话线,仿佛那根线连着弟弟的生命。
每一次铃声响起,我的心就像被鞭子抽打一下。
王桂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憔悴下去,眼睛总是红肿的。
她变得极度敏感,寸步不离地守着小雅,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仿佛一眨眼,女儿又会被夺走,或者被拉去某个冰冷的手术台。
最让我们担心的,是小雅。
那天晚上的争吵,她肯定听到了。
但她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哭,没有问,没有闹。
她甚至比以前更加沉默,更加透明,像一抹安静的影子,漂浮在家里。
她吃饭,睡觉,坐在窗边发呆。
对我们的小心翼翼和过度保护,她没有任何表示,顺从,但也隔绝。
这种死寂般的平静,比哭闹更让人害怕。
它像暴风雨前压抑的海面,你不知道底下酝酿着怎样的惊涛骇浪。
我试图和她谈谈。
我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她旁边,笨拙地开口。
“小雅……那天晚上……奶奶和叔叔的话……你别往心里去……爸爸不会答应他们的,绝对不会。爸爸会保护你。”
她缓缓转过头,看着我。
那双眼睛依旧空洞,但这一次,我似乎在那片空洞的深处,看到了一点极微弱、极冰凉的东西。
像是看透了世事炎凉的嘲讽,又像是一种认命般的麻木。
她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又转过去看着窗外。
自始至终,一个字都没有说。
我的心沉到了无底深渊。
我私下里问王桂芳:“小雅……她会不会……会不会觉得自己不该回来?或者觉得……自己只是个多余的……器官容器?”
王桂芳猛地捂住嘴,眼泪又掉了下来。
“别说了……求你别说了……”
我知道,我可能猜对了。
十年的苦难,早已教会了这个孩子察言观色和忍受。
她或许早已不相信任何无缘无故的“好”。
我们的“爱”和“保护”,在奶奶和叔叔赤裸裸的索求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她平静的外表下,究竟藏着怎样惊涛骇浪的想法?
是恐惧?是绝望?还是……一种可怕的、自我牺牲的念头?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当着王桂芳和小雅的面,拔掉了那根该死的电话线。
世界瞬间清净了。
然后,我拿出手机,给我母亲发了最后一条短信。
“妈,建国的病,我会尽力借钱帮他治,寻找其他肾源。但小雅,绝对不行。你们不要再打她的主意,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信息发出去后,石沉大海。
或者,那边已经对我这个“狠心”的儿子彻底绝望。
我知道,我和我原生家庭之间,已经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可能无法愈合的裂痕。
我选择了我的女儿。
我必须用最坚决的态度,告诉她,也告诉自己,这个选择不容置疑,不容动摇。
然而,内心的煎熬并未因此减少。
弟弟蜡黄的脸和哀求的眼神,时常在我眼前晃动。
母亲的指责像背景音一样在我脑海里循环播放。
“你就等着给你弟弟收尸吧!”
“我看你后半辈子能不能安心!”
这些声音,啃噬着我。
我变得失眠,焦虑,在深夜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王桂芳也是如此,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眼里的红血丝,相对无言。
我们守着小雅,像守着一颗不知道何时会爆炸的炸弹,又像是守着一盏在狂风中摇曳、随时可能熄灭的微弱烛火。
家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每一天都像是在走钢丝。
直到那天下午,我出去进货回来,发现家里安静得可怕。
王桂芳红着眼圈,坐在客厅里,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条。
我的心脏骤然停跳了一拍。
“小雅呢?”我的声音发颤。
王桂芳把纸条递给我,眼泪终于决堤。
“我……我就下楼扔个垃圾的功夫……回来她就不见了……就留下这个……”
那张普通的作业纸上,用铅笔写着几行歪歪扭扭、却足以让我魂飞魄散的字:
“爸,妈:
我走了。
别找我。
我去救叔叔。
欠你们的,还给你们。
……”
第六章:绝望追寻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手里的纸条仿佛有千斤重,又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手猛地一抖。
“我去救叔叔。”
“欠你们的,还给你们。”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钝刀子,狠狠地剜着我的心。
这个傻孩子!这个傻孩子啊!
她到底都想了些什么?!她觉得自己是回来还债的吗?她觉得自己的价值就是那个肾吗?!
无边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手脚冰凉,血液都仿佛凝固了。
我一把抓住王桂芳的胳膊,声音扭曲变形。
“什么时候发现的?她往哪个方向走了?穿了什么衣服?”
王桂芳已经哭得几乎晕厥,语无伦次。
“就刚才……没多久……我下楼……她就……穿着那件蓝色的旧外套……我没看见她往哪边……”
“找!快去找!”
我像疯了一样冲出门,王桂芳也跌跌撞撞地跟了上来。
我们像两只无头苍蝇,在小区里、街道上疯狂地奔跑,呼喊。
“小雅!张小雅!”
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带着绝望的哭腔,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我们问门卫,问路人,问小卖部的老板。
所有人都摇头。
恐惧和自责像滔天巨浪,将我彻底淹没。
我为什么没有再坚决一点?
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她平静表面下的惊涛骇浪?
我为什么没有二十四小时守着她?
我拔了电话线,却拔不掉她心里那根自我牺牲的弦!
王桂芳瘫坐在马路牙子上,捶打着地面,哭得撕心裂肺。
“我的孩子啊……我刚找回来的孩子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妈妈也不活了……”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颤抖着手掏出手机,第一个打给了母亲。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母亲的声音带着疲惫和不耐烦。
“又怎么了?”
我对着话筒嘶吼,声音破碎不堪。
“妈!小雅不见了!她留下纸条说去救建国了!她有没有去找你们?有没有?!”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难以置信的激动和……一丝让我心寒的期盼。
“什么?她……她自己来了?她真的来了?老天开眼啊!建国有救了!她到哪儿了?”
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沉到了冰窟最底层。
听到女儿失踪,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担心,而是弟弟有救了。
“她没去找你们?”
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
“没有啊!你们快找找!快把她送过来啊!直接送医院来!我们这就去医院等着配型!”母亲的声音急切而兴奋,仿佛一件丢失的重要货物终于自己走上了传送带。
我猛地掐断了电话。
浑身冷得发抖。
第七章:悬崖勒马
不能指望他们了。
我必须自己找到她。
她会去哪?
医院!
她一定是想去医院!
我对王桂芳吼道:“你去火车站汽车站找!我去医院!随时保持联系!”
我跨上那辆破旧的摩托车,油门拧到最大,疯了一样冲向本市最大的那家医院。
风在我耳边呼啸,像恶鬼的哭嚎。
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想象着小雅找到泌尿科,想象着她懵懂地要求配型,想象着母亲和弟弟如何欣喜若狂地接纳她……然后就是冰冷的检查,手术同意书……
不!绝对不行!
摩托车冲到医院门口,几乎没停稳我就跳了下来,踉跄着冲进门诊大楼。
泌尿科在哪里?
我像疯了一样抓住一个护士。
“泌尿科!肾内科!在哪?!”
护士被我的样子吓到,指了一个方向。
我狂奔过去,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每一个候诊的人,每一个穿着旧衣服的瘦小身影。
没有!都没有!
我的心跳快得要爆炸。
难道她还没到?还是去了别的医院?
我又冲向走廊尽头的移植中心咨询台。
就在我快要跑到的时候,我的目光猛地定住了。
在咨询台旁边的塑料椅子上,我看到了那个瘦小的、穿着蓝色旧外套的身影。
她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衣角,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像一片被遗忘的落叶。
而咨询台里面,一个护士正在低头写着什么,似乎刚刚接待完她。
“小雅!”
我发出一声嘶哑的吼叫,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小雅猛地抬起头,看到我,那双空洞的眼睛里瞬间闪过一丝惊慌,她下意识地想站起来逃跑。
我已经冲到了她面前,一把死死地抓住她的胳膊,仿佛一松手她就会消失。
力气大得自己都害怕。
“你干什么?!谁让你来这里的!跟我回家!”我的声音因为极致的恐惧和后怕而剧烈颤抖,听起来像是在咆哮。
咨询台的护士惊讶地抬起头。
“先生,您有什么事吗?这位小姑娘刚才来咨询亲属活体肾移植的事情,我正让她填表呢……”
“不填!我们不移植!什么都不做!”
我几乎是粗暴地打断护士的话,一把将桌上那张刚写了个名字的表格抓过来,揉成一团,狠狠扔在地上。
我的举动引来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
小雅挣扎着,声音微弱却带着哭腔。
“爸……你放开我……让我还给你们……让我走吧……我欠你们的……”
“你什么都不欠!”
我红着眼睛,对着她吼,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
“是爸爸欠你的!是这个世界欠你的!你谁也不欠!不用你还!不用!”
我再也控制不住,猛地将她瘦小的身体死死地搂进怀里,抱得那么紧,仿佛要将她揉进我的骨血里,再也不分开。
我的眼泪滚烫地落在她的头发上。
“傻孩子……我的傻孩子啊……爸爸带你回家……爸爸带你回家……”
我语无伦次,一遍遍地重复着,像是在对她说,又像是在对自己发誓。
小雅在我怀里僵硬着,然后,慢慢地,一点点地松懈下来。
最终,她发出了一声极其细微的、小动物般的呜咽,眼泪无声地浸湿了我的衣襟。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母亲打来的。
我一手紧紧搂着小雅,一手接通电话,按了免提。
母亲急切的声音立刻炸响在走廊里。
“建军!找到小雅没有?找到没有?直接带来医院啊!我们和建国都到了!医生我们都联系好了!快……”
“妈。”
我打断她,声音冷得像冰,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找到小雅了。”
电话那头顿时期待地安静下来。
我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的力气,清晰无比地说道。
“我现在就带她回家。回我和桂芳、小雅,我们三个人的家。”
“从今天起,”
我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决绝的恨意,响彻整个走廊,也通过手机,砸向电话那头的人。
“你们不再是她的奶奶,不再是她的叔叔!你们谁再敢打她的主意,再敢靠近她一步,我就跟你们拼命!我说到做到!”
说完,我狠狠地挂断电话,并直接将那个号码拉黑。
走廊里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看着我们。
我低下头,看着怀里还在轻微发抖的女儿,用我此生最温柔、最坚定的声音说。
“小雅,我们回家。以后,爸爸的家,就是你的家,永远都是。谁也不能再伤害你。”
我牵起她冰凉的手,紧紧地握着,一步一步,坚定地离开了医院,离开了那片几乎吞噬她的阴影。
第八章:艰难的愈合
那件事之后,我们切断了和老家几乎所有的联系。
后来断续听说,弟弟的病最终没有等到合适的肾源,病情恶化,一年多后去世了。
母亲深受打击,变得更加偏执和沉默。
听到消息时,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坐了很久。
心里有悲伤,有遗憾,但唯独没有后悔。
我做出了我认为正确的选择。
我们的生活,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艰难却充满希望的重建。
小雅似乎因为我那次在医院决绝的表现,内心深处某个坚硬的角落开始软化。
她开始慢慢地、尝试性地接受我和王桂芳的好。
她依旧沉默,但眼神里不再是全然的空洞。
她开始会看着我们忙活,会在王桂芳给她夹菜时小声说“谢谢”,会在夜里做噩梦惊醒时,允许王桂芳抱着她轻轻安抚。
我们带她去看心理医生,耐心地陪伴她。
告诉她,她不需要偿还任何东西,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恩赐。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虽然药效缓慢。
一年,两年……日子像流水一样平静地走过。
小雅的脸上渐渐有了属于她这个年龄段的、细微的表情。
她开始去上夜校,学习她错过的知识。
有一天傍晚,我们一家三口在楼下散步。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小雅走在我和王桂芳中间,依旧不怎么说话。
但当她偶尔抬起头,看到飞过的小鸟,嘴角似乎极其轻微地向上弯了一下。
那一刻,我和王桂芳交换了一个眼神,彼此眼里都涌起了泪光,却是温暖的。
我们知道,那条漫长的、通往女儿内心的路,我们终于,快要走到了尽头。
虽然过去的伤痕无法完全抹平,未来的路也未必一帆风顺。
但至少,我们守护住了最珍贵的东西。
我们让女儿知道,她不是器官,不是工具,不是用来交换的筹码。
她是我们的女儿。
我们爱她,仅仅因为她是她。
有些伤害,以爱之名,却比拐卖更诛心。
守护需要的不只是找到她,更是直面扭曲、捍卫她的权利。
家庭的真正团圆,在于心灵的接纳与保护。
伤痕或许永在手机炒股软件推荐,但爱能催生新的希望。
声明资料:本文情节存在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图片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发布于:河南省辉煌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